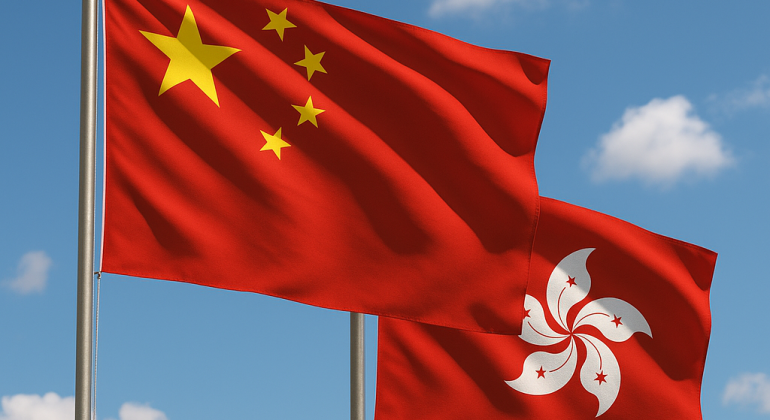【緝步成章】地緣動盪貿易站邊 兵家必爭「算力主權」
【緝步成章】地緣動盪貿易站邊 兵家必爭「算力主權」
本文作者為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王緝憲教授。文章轉載自《信報》「緝步成章」專欄(於2024年9月3日刊登)
隨著全球自由市場秩序受到挑戰,內地與香港的政府管治模式正面臨不同但相似的掙扎。在本篇文章中,王緝憲教授根據多年與兩地官員交流的觀察,指出「一國兩制」下的大小政府思維如何各自遇上制度性掣肘,並提出香港應更具政策主動性,而內地則須更依賴市場機制,以因應當前經濟與社會挑戰。
因研究和工作需要,經常與內地和香港政府官員交流,每次都會感受到兩者的不同。 最主要的一個差別,來自於政府的大與小。「一國兩制」其中的一個隱含的內容,就是容許香港成為特區後,繼續以之前的「小政府」方式管理這個城市。 25年來,特區政府架構實際上變化不小,有了不少以前沒有的局,任命方式也不同了。 然而,有一點一直沒有變:如果你與特區政府任何主管經濟、金融、貿易等相關事務的官員接觸就會發現,他們都堅信小政府大市場是香港涉身立命的成功經驗和基本原則,不可動搖。 可以說,他們腦子裡都有一條隱形但清晰的邊界,一邊是市場,另一邊是政府。 而在中國內地是大政府,因此政府官員通常習慣的思維是:幾乎什麼事情都可以插手。 然而,近來發現,兩地的官員都對目前的新形勢有一種力不從心的困惑。
香港:小政府思維難以應對新國際局勢
先說香港。 從數年前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時開始,為了自身利益,美國政府甚至美國經濟學家再也不提在世界範圍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即一般人口中的全球化,而是推行以政治體系和意識形態認同劃圈的「friendshoring」(友岸貿易)。 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自然而然地被劃入非友岸之列,這讓一貫支持徹底市場的人無言以對。 世界市場經濟一哥政府都大動作地干預經濟,小小香港特區政府還有什麼理由不作為? 不過,香港不是新加坡,知道政府以什麼方式、如何「入場」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比如新加坡有跨國「央企」「星展銀行」和「PSA」。 在香港,這從來都是離經叛道。 這裡甚至不可以提支柱產業,因為這意味著偏幫某個行業。 如果說有哪個機構在打入國際市場方面做得最好的,應是貿發局(TDC)和旅發局了:多年來,他們一直在以各種形式推動香港最擅長的貿易、旅遊和會展等行業。 然而,類似的准政府「獨立機構」比如郵局和生產力促進局,推進香港國際市場的力度,對比新加坡類似機構,微乎其微。 表面上看,似乎是它們自身不夠進取。 但本質上,是受害於跟不上形勢的傳統思維和定位,即不考慮超出傳統小政府所為的範圍。
內地:投資驅動模式的後遺症日益明顯
嚴重的供過於求,恰逢新冠清零後各級政府的財政枯竭。 即便如此,仍然有經濟專家和媒體喊出要大建新運河,包括湖南到廣西的湘桂運河、湖北的荊漢運河,江西和河南等省也在忽悠。 我無法想像,這些專家和媒體可以不知道在現代化的鐵路網和公路網遍佈的內陸省份,考慮巨資修建已經被淘汰的運河這個運輸方式是錯誤的,但我可以想像,各個內陸省,為了套得國家投資(這種超級大工程,很大機會中央政府出至少一半,即數百億),開動宣傳機器來鼓噪。 相信如果100%由各省自己掏腰包,沒有一個省會搞這種為了基建而基建,推高負債而又沒有回報的項目。 不過說到底,為什麼至今仍然還有地方政府,甚至背後可能也有中央政府的某些力量在支撐這種為了投資而投資的過度基建呢? 我以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過去40年靠投資拉動經濟「成功經驗」的思維在繼續。 而且,即使有不少明眼人已經看到這個方式已經無以為繼,但因為對市場經濟認知有限,找不到政府如何更直接刺激需求的方式,或者不存在這種機制。 正如我一北京朋友所言:「計畫和市場,從思維到組織運行機制都是不同的。 內地是體制形成的組織強大,這種思維和現實中可利用的組織資源都造成了這套(制度)長盛不衰。 」
內地需「市場化」,香港需「政策化」
香港與內地目前的困境可謂異曲同工:化解危機,香港需要更「政府」,內地需要更「市場」。 最近內地這方面最鼓舞人心的動作,就是《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提出:「消費稅徵收環節後移並穩步下劃地方,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和抵扣鏈條,優化共用稅分享比例。」這會促進地方政府把眼光和力量放到改善本地消費環境。 期望對官員考核指標也因此從GDP轉向。 香港方面,最大動作是調整政府部門設置和資金配置,以支援國際人才招攬和創科發展。 期望港府官員的思維方式也可以隨之變得更為進取。